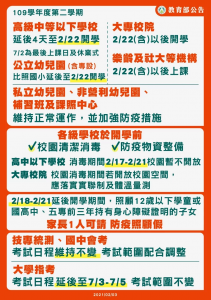2003年,顧曉軍從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,沒能順利考上研究所,他曾當過旅行社的業務,也曾在北京奧組委工作過。那段時間,無論每天工作多忙多累,他都會擠出時間學外語和閱讀歷史文獻,他對語言和中西方古典文化的熱愛從未止息。
何以會對學習語言有如此濃烈的興趣?顧曉軍表示,大學時他的研究方向是歷史文獻。當時選擇這個領域的同學不多,因為對語言的要求高,除了要了解最新的學術動態,還要去解讀各類古代文獻。
顧曉軍說,不敢說已經完全掌握了多少門語言,有的可能還算不上精通,但確實從學生時代,就嘗試自學日語,後來又學了法語、古希臘語等。歷史是包羅萬象的,掌握更多語言,能幫他近距離地觸碰到歷史上那些偉大的人物、經典的文學,體會到更強烈的心靈震撼。
2009年1月,顧曉軍到中國國圖工作,儘管圖書館員的薪資不算高,對他來說卻是一份上天恩賜的位置。
在這裡,顧曉軍除了得以接觸到各類原典和學習材料,工作條件也相對寬鬆。除上午兩個小時、下午兩個小時值班,其餘時間可以自由運用,這讓他得以恣意悠遊於國圖浩瀚的書海中。他表示,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,他很滿足。
過去這段時間,顧曉軍一得空就埋首於《游敘弗倫申辯克力同斐多》。這是一本雙語對照的柏拉圖對話集,一邊是古希臘語原文,一邊是英語譯文。這本書是春節後上架的。
顧曉軍說,他節後上班看到,特別驚喜,覺得這簡直是給他準備的新年禮物,他可以先好好琢磨古希臘語原文,再看旁邊的英語,以此來求證自己的感覺。
中國大陸媒體稱他為野生語言學家,顧曉軍說,學語言最需要什麽,耗功夫,如果他的工作也像一般上班族那樣緊張而忙碌,那很多學習計畫也就無從談起了。
對於有人稱他是圖書館裡的苦行僧,在《北京青年報》的專訪,顧曉軍說,「我真的不是,你看我哪兒苦了?沒有苦,我也沒為了喜歡的事情不吃不喝,一切都很自然。其實我覺得這樣很酷,能得到很大的滿足。」
顧曉軍指出,文字有一種美,對他來說,學語言、閱讀原典真的很開心。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松有句名言,這個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茍且,還有詩與遠方。在顧曉軍眼中,每天上班的這座圖書館就是他的詩和遠方。
「詩是一種理想中的狀態,是一種形而上的東西,而遠方是現實中的遠方。圖書館有書,你精神上無法超越的,可以通過書,看看人家是怎麼超越的;你空間上到不了的地方,你也可以找本書看看,從書中有所獲得;詩和遠方,在圖書館都可以找到,只要你想找。」
有件事╱迷戀古希臘語 想用它說遺言
現在顧曉軍投入最多時間學習的是古希臘語,一開始是為了閱讀古希臘語寫成的《西塞羅傳》,如今,卻已經被古希臘語的典雅深深吸引。它每個詞的變化非常多,一個動詞的基本變化可能就有上百個,一個名詞的基本變化也有幾十個。
這麼複雜,會顯得這種語言很不經濟。但是一旦你進入到這個氛圍中,就會發現它能表達很多微妙的東西,這種微妙,不要說中文和英語,甚至連拉丁語都表現不了。
在《新京報》的訪談中,顧曉軍說,如果哪天他即將離開這個人世間,能用古希臘語說出自己的遺言,「余致力於古希臘語之學習,凡30餘年、凡50餘年、凡70餘年等等」,他就覺得此生已經圓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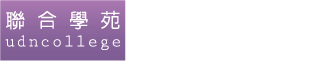
.jpg)

-300x177.jpg)